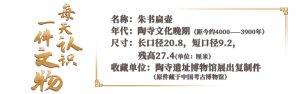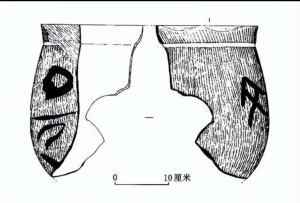我父亲是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上的学,那是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全部说英文,不算是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学校,王世襄先生也是那里毕业,我父亲比王世襄先生晚了将近十年。而朱先生上的则是正经教育体系内的中学。但是,不管在外面上什么样的学校,回到家,都有好几位专门讲旧学的家庭教师,如讲经学的、讲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还有讲史学和诗词的等等。
当时很多人家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新式教育不可废弛,中国传统的经史也不能丢弃。我所知道的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周一良先生、杨宪益先生等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相似。
朱家和赵家虽然都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朱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非常新派,不守旧。我祖父一直主张我父亲要学习新学,朱先生家更是如此。他的父亲朱文钧(字翼盦)先生是英国牛津毕业的,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在清末的度支部就职,民国后度支部变成了财政部,他做到监事、盐务署长,所以朱家和赵家都不是那种陈旧、保守的家庭。
这几位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数理化的成绩在学校都是一塌糊涂,都是文科的基因,直到我这一代,数理化也是十分糟糕的。
朱先生和我父亲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朱先生入学是1937年,毕业是1941年。我父亲入学是1943年,毕业是1947年,比朱先生晚了六七届。
朱先生在辅仁期间也是辅仁的全盛时代,他的授业老师都非常了不起,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有沈兼士先生,还有余嘉锡先生、顾随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教授。朱先生当时还帮助沈兼士先生整理很多文字学方面的教案,对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朱先生毕业时正是沦陷时期,当时谋事很困难,所以朱先生1941年到了重庆,在国民政府的粮食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那是“没法子,混饭吃”,这个朱先生对我讲过。他那时要查很多档案,要起草很多公文,对他来说如同嚼蜡,是极没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