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俄乌紧张局势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乌克兰与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关系?乌克兰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在下文中,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谢尔希·浦洛基从历史、语言、文学和民间传说的角度讲述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建构的过程。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明的断层线上,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的相遇,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充当了各大帝国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和民族气质。
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在下文中,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谢尔希·浦洛基从历史、语言、文学和民间传说等角度讲述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建构的过程。
以反波拿巴为旗帜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对任何歌曲来说,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是“波兰还没有灭亡”。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一目了然。这样的悲观主义从何而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法国皇帝——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最初叫作“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都曾参加过科希丘什科起义。这首歌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因此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看到了希望。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它应该是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并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建立了华沙公国。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祖国复国这一令人激动的前景。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Sir Thaddeus)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1815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tsardom),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Aha!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e?”)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乌克兰语与浪漫主义文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1798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Eneïda)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画像。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第一部分时,正值教会斯拉夫语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Natalka-Poltavka,即《波尔塔瓦的娜塔尔卡》)。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并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东至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Oleksii Pavlovsky)在1818年出版了其作品《小俄罗斯方言语法》(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一年后,米科拉(·尼古拉)·采尔捷列夫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也得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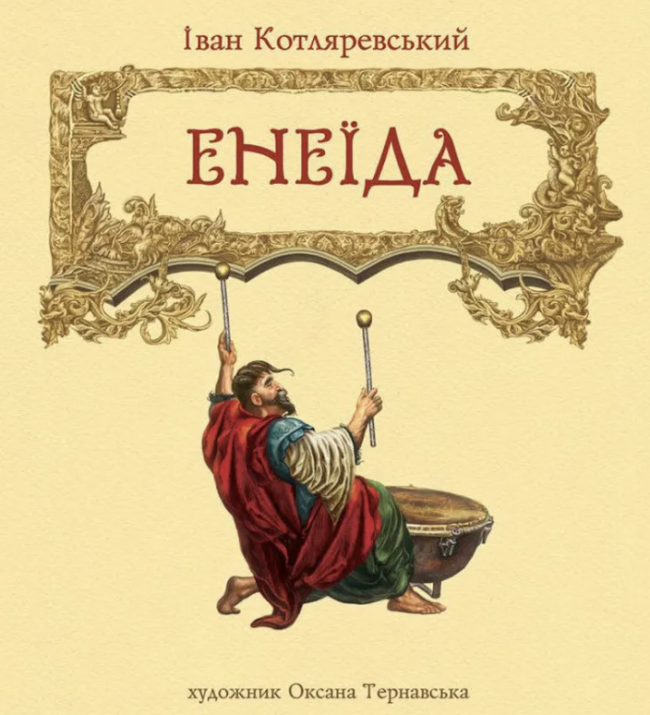
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乌克兰语诗作《埃内伊达》书封。
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一个异数而已。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都重视情感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1805年,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志和民间传说感兴趣,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它是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因此,1816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Ukrainian Herald)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但它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它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
哥萨克历史的影响
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罗斯历史》(Istoriia rusov)的积极欢迎和宣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的著作,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来自前哥萨克国斯塔罗杜布地区的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并更加公开地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

曾居住于乌克兰中心地带的扎波罗热哥萨克。
《罗斯历史》将哥萨克人刻画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并通过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们的英雄事迹、战斗历程和死于敌人之手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历史。这些敌人和其叙事中的反面人物大都代表着别的民族——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帝国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们的想象力都被《罗斯历史》点燃了。这些人中包括圣彼得堡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拉·果戈理。在哈尔基夫,这一神秘文本的主要鼓吹者是本地大学的一名教授伊斯梅尔·斯列兹涅夫斯基。与他之前的麦克弗森一样,斯列兹涅夫斯基同样自己创作民间传说。麦克弗森利用爱尔兰神话来达到目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则在《罗斯历史》中寻找灵感。这部作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前哥萨克国地区风靡一时,将一段关于哥萨克社会阶层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对一个新兴民族社群的记述,迈出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塑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曾经存在的哥萨克国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提供了砖石——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建筑师:《埃内伊达》的作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米科拉·采尔捷列夫和写出第一本乌克兰语语法著作的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都来自前哥萨克国。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中,哥萨克国精英阶层占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在奥属加利西亚和俄属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垦殖的南方草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则是族群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因此,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斗争的先锋。这个新民族从其语言到其名字“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谢尔希·浦洛基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