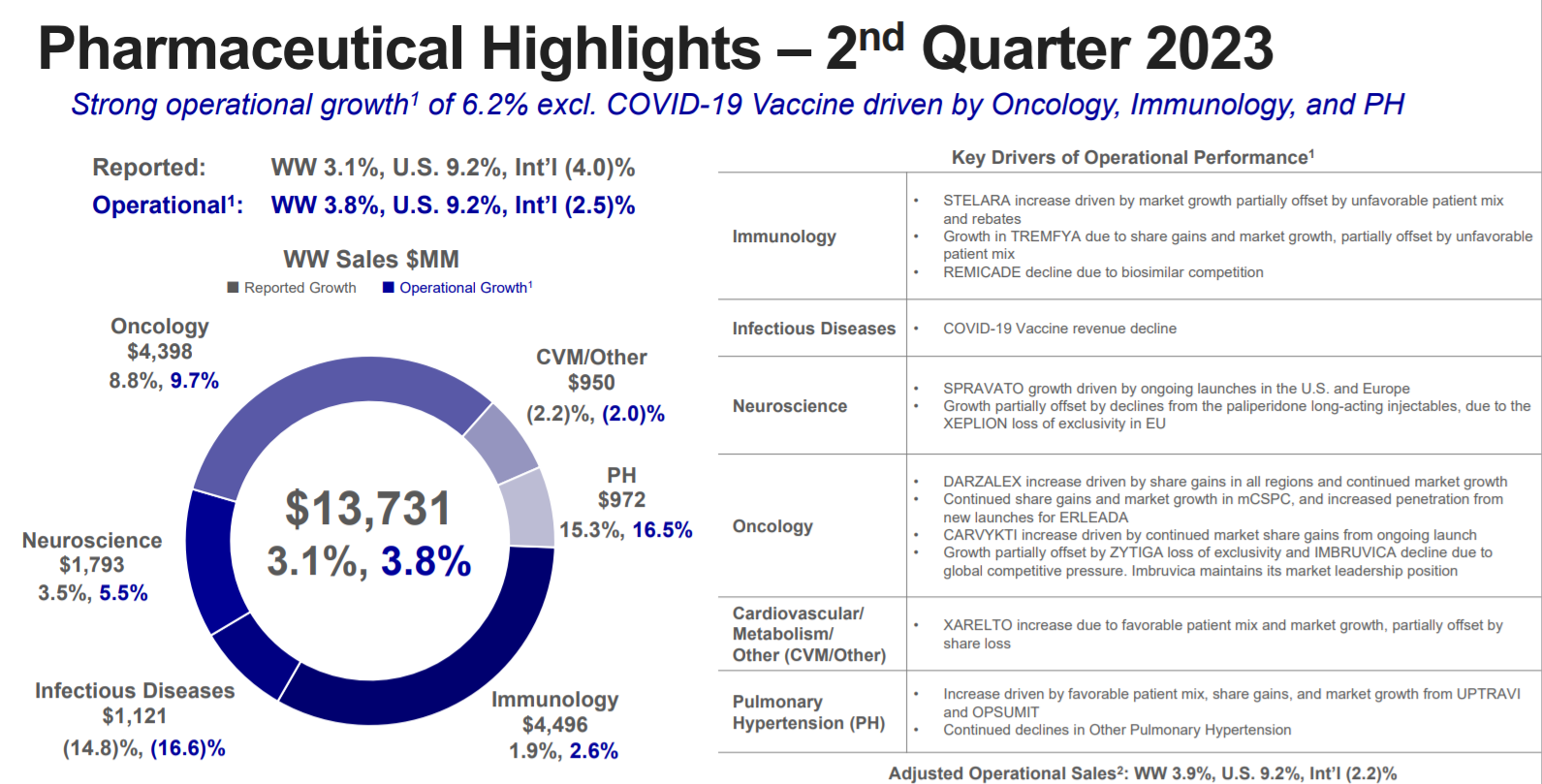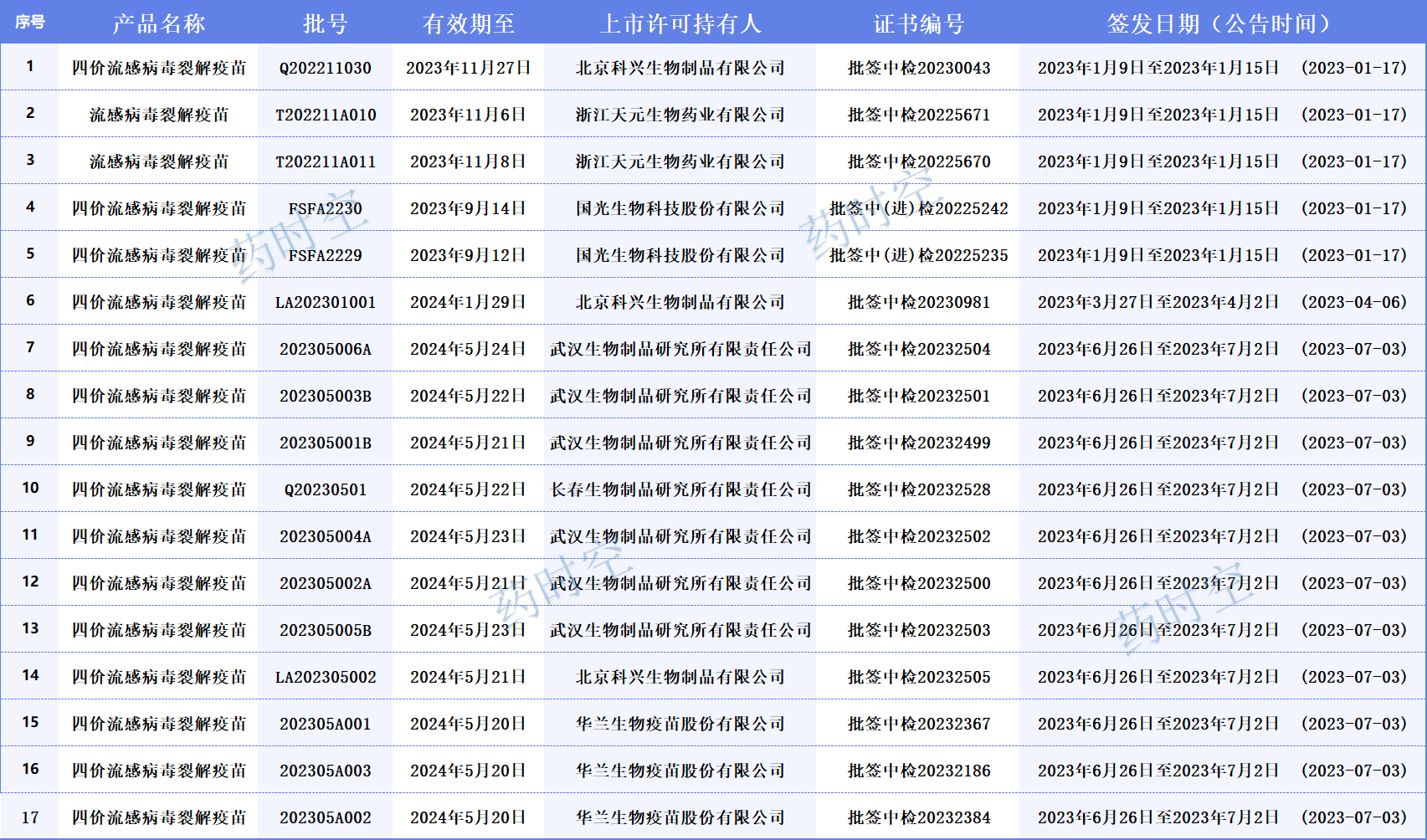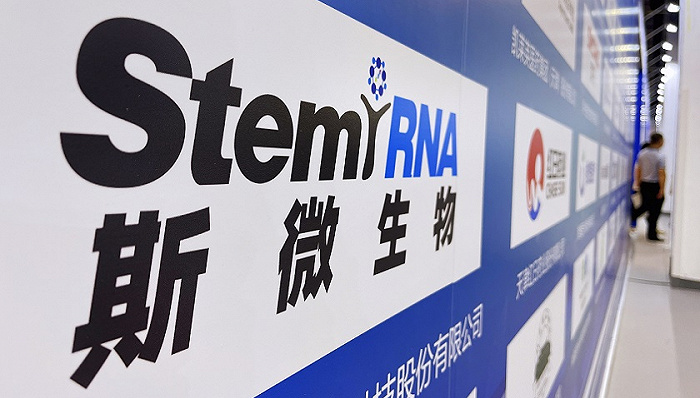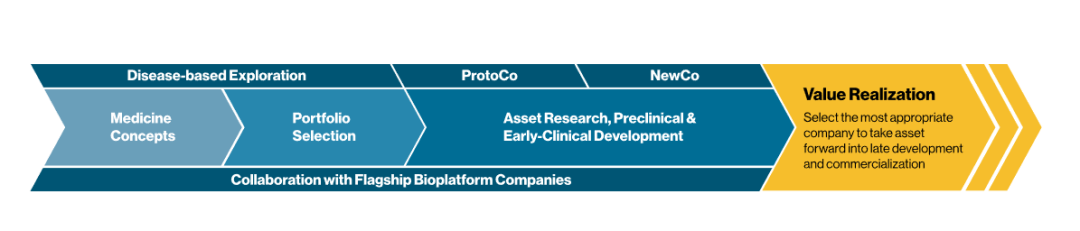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未出嫁前是斯蒂芬家的小姐。”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的第一句话,据说相当的有名。贝尔是伍尔夫的二侄子,他父亲是克莱夫•贝尔,母亲瓦奈萨是伍尔夫的姐姐,贝尔后来成了有名的艺术史家,并且给他姑姑写了这么本有名的传记。名著的第一句话总是会给人别样的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未出嫁前是斯蒂芬家的小姐”,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呢?
它有一股“冷感”。
贝尔和他姑姑关系很近,尤其是在伍尔夫晚年,贝尔同她的往来很频繁,但这第一句话,却说得仿佛不怎么认识她似的。而且通观《伍尔夫传》全书,这种陌生都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浓度上。到了1941年3月28日,弗吉尼亚投水自尽的日子,贝尔依旧写得不带半点感情,半点多余的想象和揣测:“将手杖留在河堤上,她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了外套的口袋,然后走向死亡。”换一个作者,除非补一句“水面晃动了一下,立刻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给吞没了”,否则都不愿交稿。
在《伍尔夫传》面前,我们也得把作者和传主的关系理解得若即若离一些。这是他们保持情感关系的关键,也是理解布卢姆斯伯里这整一票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昆汀•贝尔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里办报,就撺掇姑姑给自己供稿。是“撺掇”,而不是动员,按照他的认识,这就比拉人下水好那么一点点。对此,他后来还有一句解释:“放着个真正的作者在手边却闲置不用,似乎很愚蠢。”
姑侄俩的关系很好,弗吉尼亚提供有趣的文字,描述布卢姆斯伯里一圈人,以及厨师、管家、女仆们的日常憨态,昆汀配上插图。在一张合影中,弗吉尼亚用手指点着昆汀手里的书,笑容难得地不太扭曲。而昆汀,像个典型英国公学男孩那样苍白,正把他婴儿肥的脸转向镜头,那时的他大概不曾想到,自己将来会给亲爱的姑姑写一本不吹不黑的传记。
昆汀在1920年代走向成年,那时当道的,是“迷惘的一代”,《荒原》及《尤利西斯》,包括弗吉尼亚的《雅各布之屋》,都在1922年发表。弗吉尼亚那时年届不惑,小说有种淡泊的气息,有种对政治的故意疏远和对风暴未至前的安宁时刻及时的珍惜。她很清楚,自己是特权中人,随性的讥诮,故意的疏离,通过讲究的文字来保持对一切的矜持,这都是特权人士才能享用的,她也明白,特权来自专制和不公道。
《雅各布之屋》连一个鲜明的主人公形象都没有,当时的名作家阿诺德•贝内特抨击这一点,可贝内特分明就是被弗吉尼亚看不起的。她认为,像贝内特、高尔斯华绥这类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作家都过时了,在她自己的圈子里,E.M.福斯特当时已经出了四本小说,他就和弗吉尼亚是一路,也是一个不突出主角的写作者。不过,论起风格上的独特,弗吉尼亚逐渐做到了极致,而福斯特后劲不足。当1925年和1927年,弗吉尼亚连续发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这两部确立她个人地位的代表作时,福斯特都已经弃写长篇了。
弗吉尼亚的冷,尽显在她这几部作品里。而且她很以此自许。她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这篇著名的驳论中举了一个例子:火车里坐着一个简朴寒酸的中年妇女,就叫她布朗夫人吧,贝内特会如何描写她呢?他会勾勒无穷无尽的细节;高尔斯华绥会对时弊大加抨击,再把布朗夫人描绘得极其可怜;至于威尔斯,作为一个善于畅想未来的人,他一定会将布朗夫人的贫穷乌托邦化。她说,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能写出人物的灵魂,写出人物性格的实质来,这个任务是用寥寥数语来完成的,大费周章就是在犯蠢。
不用说贫寒的布朗夫人了,就是写自己显赫的父亲,她也是如此。
她的教育,是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一手包办的。小时候,她陪着父亲,带着狗,在伦敦城里四处散步,一边走一边聆听父亲的训导,回到家里,她贪读父亲图书室里的书,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再到休谟。弗吉尼亚和她姐姐瓦奈萨,一个干上了文学,一个从事绘画,都是父亲的功劳,可在文章里写到自己父亲时,弗吉尼亚的用词俭省、疏离,对父亲的慷慨,她没有正面的感激,而只是说“如今,有的父母不会让一个十五岁小姑娘随便进出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筛选的大图书馆,我父亲却认为这并无害处”。写到父亲说“读你们想读的书吧”时,弗吉尼亚加了个修饰语:不是“亲切地”或“大方地”,而是“简短扼要地”。
莱斯利的第一任妻子是萨克雷的女儿,萨克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作家,莱斯利本人的父亲是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一个大英望族的继承人。但到了弗吉尼亚这一代,19世纪谨严而牢固的传统价值都在瓦解。弗吉尼亚和她姐姐瓦奈萨,以及索比和阿德里安,这几个斯蒂芬家的孩子,把戈登广场沉重的木门后的一个名叫布卢姆斯伯里的地方,变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敦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中心。他们所做的事情则不过是谈话,是到了凌晨一两点依然供应的威士忌、小面包、可可。
昆汀•贝尔说,莱斯利爵士对弗吉尼亚的基本态度是又爱又恼。这很可信。这一圈人互相之间的感情一定是充满了挑剔的,除非得到一种矛盾性的描述,否则,这些感情根本不足为外人所知。挑剔、疏远、含混,这都是高级审美的特征,很像《到灯塔去》中的那座灯塔,既近又远,清晰又迷离,说不清有什么象征意义。弗吉尼亚这个“浪漫的势利鬼”,既光鲜又可畏,她活在自己内心的丛丛冲突之中,活在调情与被调情中,靠着才华横溢的玩笑减自己的压,活跃别人的气氛,而她那一碰就碎的身体,又不敢付出任何稍微多一点的亲密。
“肮脏的布卢姆斯伯里”是亨利•詹姆斯的说法。他在伦敦住的时候,看到斯蒂芬家的兄弟姐妹拉来一批大学同学饮宴取乐,看到阿德里安和弗吉尼亚互相扔黄油。“可悲可叹啊,瓦奈萨和弗吉尼亚上哪儿搞来这么一帮子人。”大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也是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里的人,他很有风度地说:这里的精英够伤风、够败俗的。
然而快乐又是多么短暂,回想起来,也不过就是那么短短几年。世纪之交的人,平均寿命都短得可怜,从《伍尔夫传》中看,弗吉尼亚还未成年,就不停地有人死去,有人濒临死去,先是弗吉尼亚的母亲病逝,然后是同父异母姐姐精神病频发,再是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一个曾给父亲带去有力帮助的女孩的病故,事发得很突然。1904年,父亲莱斯利去世。昆汀没有提弗吉尼亚如何悲痛,而说到她的恼火:那些不得要领的吊唁信和讣告惹恼了她,有一个来看视的女人,说话特别快,为了赶走她,弗吉尼亚“不得不尽量显出疲惫的样子”。这个细节,说明她在乎文字是否把人描写到位,更甚于在乎这个人本身,也说明她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趣味,那种对自我之高雅的热忱,有多么的彻底。
昆汀还写到斯蒂芬家的孩子们追捕飞蛾的场景。飞蛾是弗吉尼亚喜欢的意象,从它身上,她感到自己被不知名的敌对力量所追击,并摧毁。她后来写的《海浪》,原定的书名就是《飞蛾》,《雅各布之屋》里也有飞蛾,同期的散文《阅读》里继续延伸飞蛾的主题。1906年,她的哥哥索比死于伤寒,仅仅26岁,这时距她父亲去世才过了短短两年。弗吉尼亚在小说处女作《远航》里,写了一个女主角蕾切尔,她死于伤寒后,飞蛾又出现了。
昆汀在书中时而透露类似“近日无事”的意思。就这点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他似乎意识到,笔下释放出的一串串人名,读者都不一定爱看。可他又总有妙到毫巅的点评,让人不忍轻易释卷。随着二战打响,弗吉尼亚对工人运动也关心起来,参加了一些左派集会,可她跟主流左翼作家终究不是一路。昆汀说,和那些人不同,“她不指望比她社会地位低的人爱她……她没怎么体会到对无产阶级的爱,以至于她想取缔这个阶级,在此过程中,取缔整个阶级社会”。当然,她也不会表达对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阶层的爱,除非以疏远、孤冷、挑剔的方式。
除了出版作品外,布卢姆斯伯里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也就是婚嫁了。1907年,瓦奈萨嫁给了克莱夫•贝尔;1912年,弗吉尼亚嫁给了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当时写给维奥莱特的信,写得很见性情:
“我有事要向你忏悔。我要跟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了。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我感到那么幸福,超过了一切人的想象——可我坚持你也要喜欢他……我们一直在谈你的很多事,我告诉他,你有六英尺八英寸高,还有就是你爱我。”
她真是会享受语言。写到“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时,她大概自己都笑出来了,这差不多就相当于“不敢宰鸡的厨师”吧。而“我坚持你也要喜欢他”一句,则表明她深受乃父的熏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易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否则她就该写“你一定会喜欢他的”了。至于最后这句,是典型弗吉尼亚式的淘气,语言中的谐谑,“滑稽感”,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也是他们同上一代贵族之间拉开距离的主要特点之一。
昆汀•贝尔的书,基本上将人们对一个女小说家的想象给打碎了。弗吉尼亚跟任何走情感小说路线的“女作家”都完全不一样。即使读过她的随笔和散文,一般人怕也不能想象,在现实之中,她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多少正统“女人味”的女人。至于“女权主义先驱”之类的说辞,也在贝尔的书里被一举驱散,她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19世纪的一面忠实的镜子,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篇名文,可她从未对家庭这个束缚女人的牢笼横加指责,她只是坚持自己的写作欲望不容窒息。布卢姆斯伯里给了她全部的庇护,她封闭在这个很小的圈子里面,不曾踏足一个小酒馆,不曾在公共厕所里下蹲,不曾在集体宿舍里住过一宿。她在比如《三个基尼金币》中对女性的捍卫,是基于对外部社会过时的理解。
昆汀并不是有意用冷感的笔触去描写姑姑的一生的。是布卢姆斯伯里的文化要求他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必需的趣味,虽然时有讥诮,可是既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在读者眼里,这部传记保持“客观视角”的可贵品质,在他那里只是基本的素质罢了,而这份视角,在书中,不时得到了传主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文字的肯定。1940年11月,为了躲避空袭,弗吉尼亚搬到了乡下,她写信给友人维塔,感谢她在这个物资短缺的时刻送来的黄油。她感谢朋友,赞美黄油,可这感谢和赞美又掺了多少保留,多少臭贫,那是她毕生维持的趣味的证明:
“我但愿自己是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话,我就能对你表示感谢了。自我那颗破碎的寡居之心的深处……我说,那是一整磅黄油,边说边掰下一小块,就这样干吃了它。于是,在踌躇满志之下,我把我们整周的配给黄油——它大概有我拇指甲的大小——都送给了路易——赢得了永生的感激;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面包和黄油。加上果酱本会是亵渎神圣的事……请代我向奶牛们致以贺词,还有挤奶女工,我想建议那只牛犊将来(如果它是男的)叫做伦纳德,如果是女的,就叫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英]昆汀•贝尔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责编: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