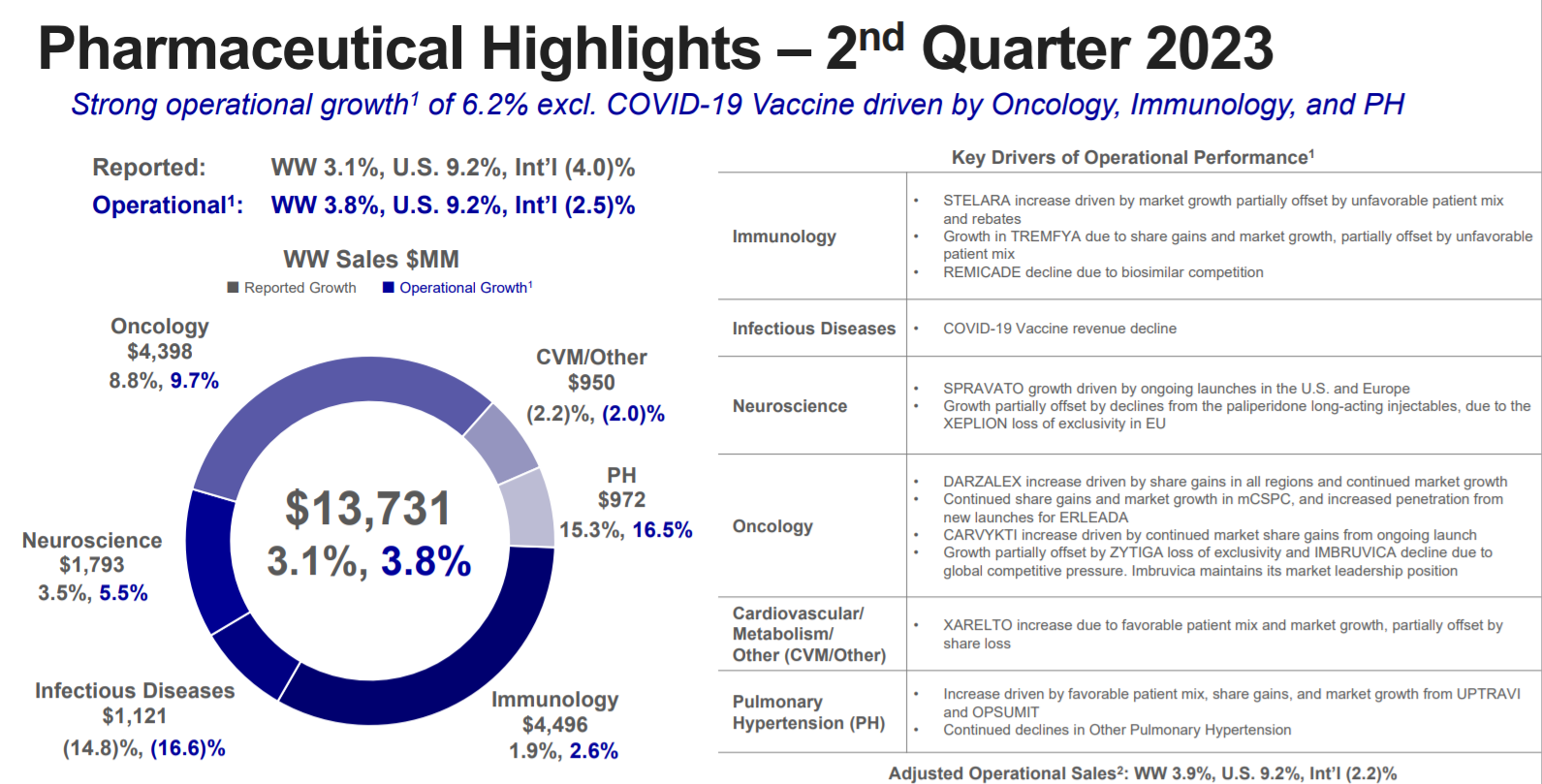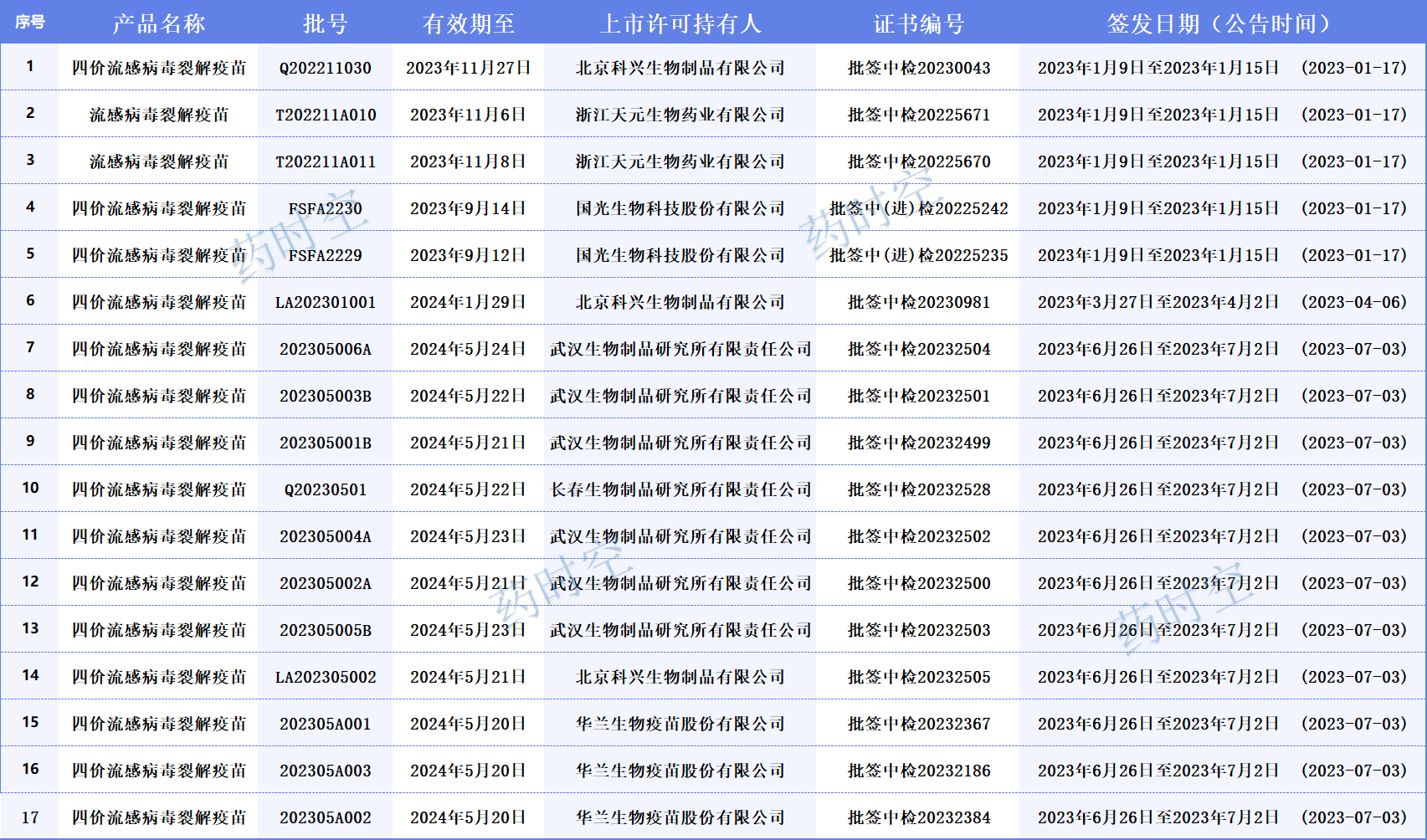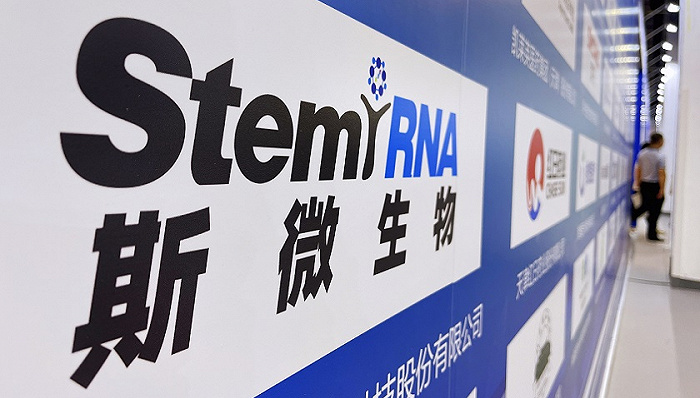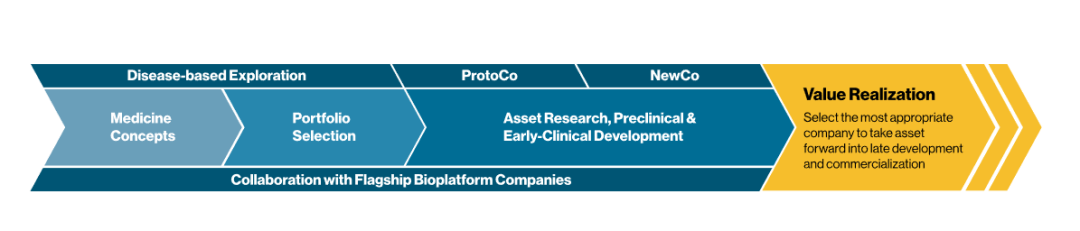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呈现在人们眼前通常都是一些政治、军事的“大事件”,这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让人忽视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很多军政大事都需要钱,尤其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1862年,新任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下院的首场演说中宣称:“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确实,他在此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通过三场战争,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因自己当年这番强硬的宣言,博得了“铁血宰相”的名声。但就算是他,完成这一功业其实靠的也不仅仅是“铁与血”,还有“金”。
对政治家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弗里茨•斯特恩在这本《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中已清楚地洞见这一事实:尽管俾斯麦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和保守主义政治家很少公开提到钱,但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他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事实上,在他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时,他所鄙视的议会都拒绝拨款,如果不是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他大概只能另谋出路:要么放弃自己的蓝图,要么向议会屈服。1864年联合奥地利对丹麦进行的一场小型战争,耗资就达到往年盈余的三倍,而议会拒绝批准还意味着俾斯麦此举本身就是违宪的;尽管他鄙视阁僚们怯懦而缺乏想象力,但在他的冒险成功之前,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在于“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
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通过自己多管齐下、见机行事的可怕手腕,一次次都成功了。他永远都会同时准备多个选择,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迅速地抓住时机去实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有利的那一个。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那个时代一流的银行家,在幕后为他做出了极为重要但却不为人知的贡献。布莱希罗德的筹资能力、理财手段和遍布各地的财经情报网络,不仅确保了俾斯麦的个人资产,使得他能在议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弄到钱,强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甚至还能比外交官提前八天迅速获知各地发生的政经要闻,这也使得他能在时代复杂变动之际,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一个由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当然,这也强化了俾斯麦的政治地位,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不用向议会让步来获得拨款,这是事理之常——在1697~1822年间,葡萄牙国王由于从南美洲获得的黄金等新财富,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都不再召集议会。
在早期欧洲历史上,曾有许多银行家专门为政府运作贷款,比如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后,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向佛罗伦萨银行家借钱,但他们从未像俾斯麦和他的犹太银行家这样,达到如此深层次的紧密结合。19世纪的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其实已逐步可以通过税收或发行公债、贷款来筹集到资金,然而这种财政权力通常都掌握在议会手里,限制执政的国王和首相的权力,以免他们的挥霍或冒险将国家拖入破产的境地。俾斯麦后来的成功使他免于被追究,证明了自己确实比议员们更有远见,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他绕开了宪法规定的议会体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为了确保自己的蓝图能贯彻实施,不惜通过非正式渠道另辟蹊径。他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利用被扣押的没收资产建成的韦尔夫基金,以便不通过公共审计使用它来贿赂、操纵记者和媒体。你可以说他达成了目的,将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但这样不择手段地灵活行事显然也腐蚀、破坏了原有的制度。
在当时的反犹声浪中,有一种论调暗示,俾斯麦不过是他身后那个犹太银行家的金钱力量所操纵的傀儡。这让俾斯麦极其恼火,无疑也背离事实:别说是“操纵”,两人之间甚至都谈不上是“合作”,因为彼此本就没有平等的基础。确切地说,布莱希罗德倒不如说更像是俾斯麦忠诚的仆人。虽然这位犹太银行家在焕然一新的德意志帝国已是首富,拥有令人嫌憎交织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仍然从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他的焦虑、不安和挫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可说预示着几十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
不错,这个新德国以远超欧洲传统强国的速度狂飙突进,但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这也是一个社会巨变、充满焦躁不安的时代。相比英法,德国的现代化显得特别快速和浮夸,那些原本出身边缘或低下阶层的群体,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赚足了钱,这愈发使原本的精英阶层憎恶现代化。老派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奉行荣誉、节俭、责任和自律的简单生活准则,渴求金钱的念头本身就令他们厌恶,因而他们虽有求于布莱希罗德,但又厌恶这么做;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如此喜欢银行家为他们理财,却又那么讨厌他的行当,因为“正派人”是耻于谈钱的,尤其不会通过商业欺诈手段来赚钱。
如果以为这只是保守倾向的德国精英的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现在看来,通过公平对等的市场交易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商人多是通过不光彩的狡猾手段赚钱的,一个腓尼基商人被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角色,而英雄人物则是通过战争或掠夺获利。在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不会让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看来,若不撒谎、欺骗、作假、贿赂,一个商人又如何获利?可是这种优越感并未妨碍老加图、西塞罗等上层人士从商业活动中获利——当然都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贵族也以好逸恶劳、鄙视工商业而臭名昭著,在话剧中被讥讽为“只有从娘肚子里出来时使过一点劲的人”,他们的资产都由管家、经纪人代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正是这一传统最后的一幕。
这种优越感在传统牢不可破的时代还算无可厚非,但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动摇了这种社会结构的根基。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流动性的社会,这势必造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人们的社会声望与其财富地位无法匹配,“穷贵族”和“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几乎是各国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发现,当地有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步行绕道一英里,而他的司机作为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仍是贱民这一事实。
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由于大批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战死,遗留下来的贵族群体原本就仅有稳定的数千人,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又被逐渐剥夺,因而社会总体上比较能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破落贵族和富商联姻,皆大欢喜。尽管如此,在整个18世纪,也只有3%的贵族男性娶了富商之女,而直至1832年,政府所有要职也几乎仍由土地贵族独占。1856年,棉纺织工厂主爱德华•斯特拉特成为第一个受封的“工业贵族”,通过将那些出身低微但具备杰出才干者封为贵族,英国确保了原有制度的弹性。不过,直至20世纪初,仍有一位上院的世袭议员抱怨首相劳合•乔治将一些新爵位给予那些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百万富翁,当有人问他“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
在英国这样相对自由宽松的国度,尚且花了两三百年时间过渡,像德国这样贵族人数更多、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更为保守、现代化进程却又更为迅猛的国家,这一转变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压锅一般的不满: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相应财富和成就的人,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那些死守固有理念的传统精英,则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暴发户,认为他们不过是通过投机和不正当手段才获得所谓的成功,要让这些不安分的异类和自己平起平坐,那真是对所有社会精英阶层价值观的侮辱。更为棘手的是,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中获利最多的还是犹太人这个一直以来遭到嫉恨的边缘少数族群,这几乎为全社会涌动的怨恨、沮丧、偏见和憎恶提供了现成的靶子。
在这一点上,正可看到像德国这样原先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论上说,现代社会应当不问每个人的出身、血统,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在他们获致成功时予以承认,但现实中远非如此。对19世纪末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成功背后险象环生:他们的财富非但不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地位,反倒强化了大众原有的偏见和嫉恨,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不是去完善市场机制,而是指责犹太人的贪婪、投机应为此负责。与此同时,相比起邻国,普鲁士的社会流动性也尤其低:旧贵族极不情愿将有影响力的犹太富豪册封为贵族,仿佛这是拿了不干净的钱来充实自己口袋。在整个1870年代,威廉一世总共只擢升了两位银行家为贵族。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必然带来的那种阶层模糊相反,德意志帝国总体上仍是一个阶层分明、难以逾越的世界,社会精英将“荣誉”看得比“财富”重要得多。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笼罩下,德国的资产阶级只是权力的影子,他们无法自信地站在舞台上。正如本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就像这个帝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贵族。”根本就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一直发育不全,因而市民阶层从未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这对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产阶层,在跻身新富群体的同时却毫无保障,这样,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战争这样的紧急状态,他们往往就是混杂着仇富与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这不仅仅是布莱希罗德或德国犹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仅仅是德国的悲剧,而是每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必上的一课。在美国这样原本就没有封建贵族的国家最为简单,几乎不经过阵痛就能度过镀金时代,但越是那些传统社会结构缺乏弹性的国家,这一过程就越是痛苦漫长。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冲决一切,即便是印度那样几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都已经造成“百万叛变”的社会不满,因为最终只能是社会结构重组来与新情况吻合,而无法将新事物重新塞进旧的紧身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犹太人是以他们的受难,告诉了我们这个惨痛的教训。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1月版
责编:李刚